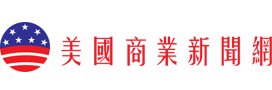圖:段國欽(前排右)與團隊守護港珠澳大橋經历了多場臺風
(美國商業新聞網)「即使我們的起步是0,我們往前走一步就會變成1。」港珠澳大橋建設前,中國在此領域的技術積累幾乎是空白,過去九年的工期,逾萬名建設「橋楚」奮戰三千日夜,創下了多個世界級工程紀錄。超級工程背後,多少無名英雄在默默耕耘,「我們走的,是世界最長、行走難度最大的『鋼線』。」從0走到1,他們鋪好了橋,亦鋪好通向世界的路。
走世界最長難度最高的「鋼線」
「從0到1,我們沒有任何先例可循。」林鳴與團體負責建設的島隧工程,是港珠澳大橋工程難度最高的部分。12年前,49歲的他剛接過這項「超級工程」的指揮棒時不無憂慮:「我國建海底隧道技術,在外國專家看來,就是小學生的水平。」也正是這群「小學生」從零起步,過關斬將「啃骨頭」,硬是打造出世界級沉管隧道的新標桿,亦樹立起中國由基建大國向基建強國邁進的技術自信。
當今世界只有極少數國家掌握外海沉管建設核心技術。港珠澳大橋建設前,中國在此領域的技術積累幾乎是空白,即便花上天價的諮詢費用,也買不來核心技術。
林鳴接受媒體採訪時對當年的經历記憶猶新:他帶隊去國外「取經」時,對方只讓他們在距離沉管隧道拋石整平船數百米遠的水域繞了一圈;而歐洲一家公司則開出了一億多歐元的技術諮詢費,按照當時匯率相當於十多億人民幣,更有外國專家篤定地說:「你們自己是沒能力做這件事情的。」
「從0到1沒有任何先例可循」
工程籌備階段,林鳴團隊掌握的全部建設經驗資料,只有一張三年前在網上公開發表的沉管隧道產品宣傳單頁。面對重重技術封鎖,林鳴拿起這張宣傳單頁,帶領團隊開啓了一系列世界級難度的技術攻關,他們首先從充分的研究論證開始。「即使我們的起步是0,我們往前走一步就會變成1。」林鳴說。天馬行空的頭腦風暴與腳踏實地的研究論證,匯集成一次又一次充滿艱難與曲折的討論爭辯。
一天午飯後,林鳴帶領團隊成員就項目的一個工程環節的可行性進行研討。討論激烈,卻一直沒有達成會議研討的成果目標。林鳴的習慣大家再熟悉不過─「決不開沒有結果的會議,決不做沒有成效的討論」。
不知過了多久,討論終於柳暗花明。林鳴疲憊又興奮地宣布散會,隱約感覺已經過了晚飯時間,他還叮囑大家吃點夜宵、早點休息。大家面面相覷:「哪還有夜宵?是該吃早飯了!」原來,已是早上六點多。這樣的討論會議,林鳴每年都會帶領團隊召開上千次。
外海沉管隧道安裝因其難度巨大而被形容為「走鋼絲工程」。「我們走的,是世界最長、行走難度最高的『鋼線』。項目施工前後需要經過幾百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做到零質量隱患,而項目上有上千個崗位。」林鳴說:「這是一場上千人一起『走鋼線』的持久戰,必須拿著『顯微鏡』去走,嚴之又嚴、細無止境。」在團隊成員看來,林鳴的「合格」標準,總比國內乃至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還要嚴苛一分。譬如,隧道中的管廊下隔牆的混凝土澆築,國內最嚴格的規範允許的軸線偏差是8毫米,但他將該誤差控制在了3毫米之內。
養成獨特「望聞問切」管理法
多年來,林鳴養成了一套獨特的「望聞問切」式工地精細化管理方法。每次到工地,林鳴都在兜裡揣一副白色手套。檢查設備時,他不只查看日常保養記錄,更會戴上手套,這裡摸一摸,那裡擦一擦,以確保設備的維護效果「名副其實」。他的「顯微鏡」不但放大表面,還透視內裡。工地的機械設備不僅要「常洗澡」,還要每周「稱體重」,如果體重上升了,那說明器械內部清洗不到位、存有殘渣。
「林式『顯微鏡』既嚴又細,這份『嚴』已達到『嚴苛』,而『細』也近乎『吹毛求疵』,但因此凝聚出了一支高質效的建設團隊。」大橋島隧工程完工驗收專家表示,相比世界同類工程沉降一般在15到25厘米,港珠澳大橋海隧整體沉降不超過5厘米。
從「當年動工、當年成島」的東西人工島施工奇跡,到精準堪比「太空對接」的33節巨型沉管「深海之吻」……幾年來,他們相繼攻克了一系列世界級難題,完成技術創新64項,形成專利400多項,構建起一整套代表世界工程頂級技術的《外海沉管隧道施工成套技術》體系。
40多場臺風考驗 毫不動搖
「大橋安全、正常。」超強臺風「山竹」於9月16日正面襲擊廣東,港珠澳大橋迎來開建以來最大的考驗,橋上測到瞬時最大風速為55m/s(風力16級),但大橋挺住了,段國欽一直揪著的心才放下來。像這樣的應急值守,現年44歲的段國欽和他的安全環保部同事,已經經历了數十次。
大橋地處珠江口的伶仃洋海域,每年平均有三四個,甚至五六個臺風過境。開工至今,大橋平安扛過了40多場臺風,撤退的人員累計近3萬人次、船舶2000多艘次,沒有施工人員因臺風傷亡。
安全「隱患」 逾萬人同時作業
這樣一個超級工程,即使沒有臺風,任何瑕疵都可能會敏感地牽動全世界的神經。因為大橋橫跨珠江口,這裡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水域,也是中國密集度最高的港口群,日平均船舶流量達4000多艘次。同時,這裡水文和氣象條件極其多變,水上交通事故易發,也是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而工程最大的安全「隱患」還在於,30多家參建單位聯動300多家輔助建設的港航企業,分散在橋、島、隧、船、廠等不同地點、不同環境條件近1.4萬名施工人員同時作業。
大橋的創新建造工藝也增加了安全的挑戰。譬如,推行「工廠化、大型化、標準化、裝配化」理念,帶來大量的海上運輸和吊裝。其中,超過1000噸的大型吊裝就有一千多次,從陸上預制場到海上施工點,最遠航程60多公裡。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發生起重傷害、高處墜落、淹溺等事故。
在這種龐大的工程背景下,安全環保部便應運而生,當時已是工程技術部副部長的段國欽應急跨界「補位」,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轉變。
鋪好橋鋪好通向世界的路
地處伶仃洋海域的港珠澳大橋,不僅容易得「三高」(高溫、高濕和高鹽)癥狀,而且是最大的「面子工程」。張育才擔任總工程師的大橋主體工程CB07標項目,承建的橋面鋪裝面積達42萬平方米,單體橋面鋪裝規糢世界第一。為了配出最為適合大橋環境的瀝青配方,張育才帶領團隊反複試驗,在兩年內用掉近100噸瀝青、500多噸混和料。
創新瀝青體系工效
張育才追逐「面子」的日子可追溯到2013年春節,35歲的他接到大橋加速加載試驗科研課題的緊急任務,要為大橋鋼橋面鋪裝的結構設計方案的選擇提供技術支持。
當時,該結構設計方案在世界範圍內未有先例可循,與之相近的香港方案也同時在對比試驗中。張育才團隊在不足一年半裡,通過大量的重複試驗、研究、優化和場地試驗段,獲得了大量的寶貴數據和經驗,通過了加速加載試驗,最終形成全新的GMA澆註式瀝青體系。
據GMA體系與香港的MA體系對比試驗證明,兩者性能相當,GMA的工效卻是MA的兩倍以上。這為大橋鋼橋面鋪裝全面採用國標GMA體系在工期與質量的雙重保障上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
進入2014年6月,張育才面臨更大的挑戰,領銜單體橋面鋪裝規糢全球最大的大橋主體工程CB07標項目。「大橋所處的『三高』環境對鋼箱梁橋面腐蝕性極強,防水、防鏽、防腐等工序必須做得更為精細。」在試驗室內,張育才團隊在兩年內用掉的600多噸瀝青與混和料,至少可以鋪裝成港珠澳大橋240米長的橋面。為解決澆註式瀝青容易產生氣泡鼓包等一系列問題,張育才團隊還設立3000平方米的專用試驗場地,對33種不同材料的組合,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新的評價標準和評價方法。
「他經常在橋面鋪裝一蹲就是一整天,平時話不多,但一出口總能點出問題的關鍵。」張育才團隊的成員透露,譬如鋼橋面防水層噴塗試驗結果達到標準,但用量均勻度未達到預期,他堅持反複的試驗,通過工藝改進將均勻度穩定在95%以內。
多年的心血汗水,大橋橋面鋪裝終於在今年2月通過交工驗收,鋪裝層的各項技術指標均達到或超過了國際同類項目領先水平,並形成一套大橋橋面鋪裝技術標準,為後續類似項目「鋪好路」。
© 2018, biznews.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