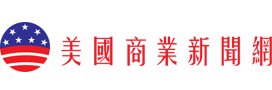《念楼书简》收录出版家锺叔河先生书信近四百通,其中致本文作者杨向群的信件七十封,是收信最多的一位。(秦颖/图)
收到《念楼书简》(九州出版社,2023),照例打电话告诉锺叔河老师,他听闻我收到的是硬纸精装,便说,过几天寄两本布面精装的来。又叮嘱一定要注意血管健康,心血管出事一下过也就算了,脑血管发病像他这样就很麻烦。“我哥哥去世了,离一百岁只差一天。”即便是几次中风,锺老师的思维从不断片,无论岔开多远的话题,他都能完美连接上。他说,告诉你一件事。长沙有个年轻人读了这本书,跟别人说——不是跟我说——看了这些信,尤其是给杨向群的那几十封,都要流眼泪。“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流眼泪”,锺老师轻声自言自语。我心说,我知道。但没出声。
书中收了锺老师从1991年到2020年间写给我的七十封信。我已经倾囊而出,实际上还不是全部。我给锺老师的第一封信,是刚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不久,他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临走留下当时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鲁迅全集》的朱正老师的联系地址,交待有事就写信请朱老师转。那正是陆续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单行本的时候。有一天接到排字车间匡师傅的电话,要我去新华印刷一厂解决问题。原来是戴鸿慈出使日记的封面上丢失了一行字。其时我才入职个把月,还不熟悉出版流程,就直接写信给锺老师,怕表达不清楚,画了一个封面的示意图,用小方框标出缺字的位置和个数。锺老师回信了吗?还是出差回来后才补上的?暂时没找到这封回信。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1986年我调来广州,到1991年有五年的时间,跟锺老师一直有通信联系,其间他带岳麓书社的编辑来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商谈《海国图志》出版事宜,要我多向常绍温先生(1923-2004)学习,游越秀公园看到“古之楚庭”牌坊,建议我用“楚庭”作为儿子的名字,场景历历在目。可惜这前后的信也一封都没找到,只有照片在手。记得锺老师回长沙后来信说,最好把底片也寄给他,我还真寄了的。
后来的信就都印在书里了。再后来就多半打电话了。有一次打电话聊闲天,锺老师说,有几位从广东去长沙的先生到念楼访他,说起谁,又说起谁谁,都是跟我先后脚到广州的同行,“好像都不认得你”。我说,像我这号不出烟丝的(湖南俗语,没有突出表现之意),人家当然不认得。他老人家倒也不以为忤,笑得很是宽容。我猜那位“要流眼泪”的长沙青年,正是从信里看到了锺老师对一个几十年都不出烟丝的后辈的温暖殷切的期望和帮助,而这些内容在他给同辈学者先生们的信中是难得有的。再者,锺老师给我的信都是随意走笔,更为自由不拘,不经意记录了许多不可复制的思想瞬间,这就尤为宝贵。书中已经收录的,这里就不抄了,再分享两则他写在赠书扉页上的短笺:
杨向群君三十年前同编“走向世界丛书”,三十年后又参加丛书补编的工作,今一百种已告完成,特将此第一种谢清高《海录》赠予,请留作纪念。因为书总会比人活得长久,人不在了,书还会在的。(《走向世界丛书·海录》,岳麓书社,2017)
即使不畜纸笔,平日用手机发短信,也可以用心一点,把文字写好一点,亦未必是为了给别人留好印象,就等于是自己洗脸梳头拔起鞋后跟再出门罢。(《给孩子读短信》,现代出版社,2020)
这样的文字,是不是既有营养,又有趣味?
以锺老师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能挺过来的。但他很少说苦难,跟我说得最多的只有两件:读书,做事。从湖南日报社扫地出门,他还能急中生智,在旧书店里巧购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见书籍在他价值观里的地位;看他在街道拖板车时写给周作人信的笔迹,仿佛能感应彼时他心中的那束光;听他讲在洣江茶场如何做一双特制的长竹筷夹坛子菜,会理解他沉浸式的编书写作就相当于另一种状态的津津有味。五六年前,我回湖南去看锺老师,正赶上他家架了大小机器,记者主持人灯光师化妆师十几号人在忙碌,他们顺便问我:你当初跟锺先生一起工作,怕他吗?我随口答道:“怕什么呢。”无论作为主编还是总编辑,锺老师对做书要求极严,却从不装腔作势。
跟锺老师见过不少大阵仗。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和法新社记者来采访他,在新华社驻湖南分社招待所锺老师和朱姨暂住的单间里,当然是因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不同凡响。至今仍能回忆起女参赞金发碧眼瘦高个的模样;也记得锺老师讲历史进程时比划弹簧的手势,口音跟他四十年后在许知远的节目中背诵“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一样,缓慢的,长沙话。后来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全国中文书展,也曾派拍摄团队到岳麓书社采访锺老师,我和其他参加丛书编辑的同事在旁边做伏案看稿状。还有香港青年学生为写学位论文专程到长沙找他。1980年代末,锺老师的《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目前,锺老师的书信集已经出版三种:《锺叔河书信初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谷林锺叔河通信》(文汇出版社,2021)和《念楼书简》,似乎还没有收录来自香港和海外收信人的信件,相信应该有的。问过锺老师怎么写信又快又好,他说进湖南报做记者跑采访,晕车反应太大,就调到通联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报社的规定是每信必回,那时候就练出来了。
其实,我手头还留着一封关于我的最长的信,是锺老师写给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职称高评委的推荐信,写在20×15规格的原稿纸上,满满五页,末尾落款处郑重其事地留着邮编地址电话,并签名盖章,时为1999年9月10日。信后附有两页剪报,也工整地贴在稿纸上:一为信中引用的李一氓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关于《走向世界丛书》的书评;二为我署名发表的第一篇小文《〈侠隐记〉和〈续侠隐记〉》。当年读信的心情渐已淡忘,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毫不犹豫地把这封信扣留下来私藏了,没有递交给“评委同志们”。虽然那年申报正高没能通过,我却从来不曾后悔。
锺老师信中所附《〈侠隐记〉和〈续侠隐记〉》,发表在1983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是锺老师布置的作业,他说书评书介就是编辑必须掌握的应用文。当时本来位于五一路的长沙市新华书店在装修,正巧搬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对面的展览馆里营业,我便利用午休时间去临时抱佛脚。在书架上找到一本茅盾著《世界文学名著杂谈》,赶紧买下,连仿带抄凑了一篇。锺老师快速地看了看,嘴上说:你还是有做编辑的资质的,一边把案头上的东西挪开,动手改起来。他的很多《走向世界丛书》的叙论,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成的,300字的稿纸,一格一字,不用誊抄,只是开头可能多费几张纸,不满意扯下来搓成团扔进字纸篓。这次很快就完工了,也没再说什么。直到报纸来了,我认真一看,那基本就是他重写的。比如大仲马在晚年曾说,《基度山伯爵》还不如《达特安三部曲》,伍光建的译本曾“使读书界为之耳目一新”,以我的学力还真写不出来。1984年,岳麓书社从湖南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锺老师被调去任总编辑,我提条件要配一部自行车(后来被锺老师引为笑谈),也如愿跟了去,仍然编辑《走向世界丛书》,但锺老师已经有了自己单独的办公室,我们几个则在楼上的编辑室写边批、编索引。两年后我嫁狗随狗到了广州,不时收到岳麓书社寄来的样书。有一天收到锺老师的信,内有一本小册子,是岳麓版新书目录及书评序跋,其中就有《〈侠隐记〉和〈续侠隐记〉》,仍然是我的名字,还特别在这一篇的标题前用红笔画了一个醒目的小三角。
锺老师说“忙完手上的事再寄”的布面精装书信第二辑,果然成了我那天晨起开门的惊喜。邮政快递单上仍然是锺老师的亲笔字迹,两层包装严丝密缝,比电话里说的多寄了一本,共三册,其中一本写了题签,另附有一纸短信。书中2001年的两封信中提到黄永玉和《陈宝箴集》:“黄永玉把你组织的《陈宝箴集》的作[编]者给他的信给我看了(其中提到了杨向群,看来特别亲切)。陈氏父子(宝箴、三立)之集均可出,三立(散原)文人,似更值得出也。”因这件事情与我责编的《陈寅恪的家族史》的作者张求会有关,我即用手机拍下发给他,张教授回曰“好多故事”。确实。收信人的年龄跨了三四代,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都有,南北东西,各行各业,有教授有小学生,有同行也有病友。其中我熟悉的好些,就是锺老师写信介绍认识或听他说过的;信中写到的一些事做成了,一些事则徒留遗憾;还有很多人、很多事值得详细解读。而我现在想说的是,唯愿锺老师康复,早日完成他的自传,让如我一般在他编辑和著作的书中受惠的人,能够像他一样眼光普照,多一些对世界的了解和热情,多一份自信和勇气:“走向世界?那还用说!”
© 2023, biznews.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