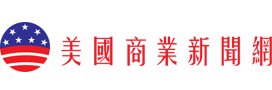7月4日,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受骚乱影响城市的政府代表开会。(新华社/路透/图)
2023年7月10日,据新华社报道,法国政府9日颁布政令,禁止在7月14日法国国庆节期间销售、持有、运输和燃放烟花,以“防止节庆活动期间的公共秩序被严重扰乱”。
据法新社报道,烟花禁令有效期为14日和15日两天,但各地市政部门和专业人士组织的节日烟花表演不受影响。
为避免骚乱再起,法国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承诺,将在法国国庆日的周末采取“大量措施保护法国人”。
6月27日,17岁北非裔少年纳赫尔因拒绝路检被警察击毙,引发从巴黎大区向全国多个城市蔓延的抗议和骚乱。
近年来,因某一突发事件或政府某项决策引发抗议,随即升级为骚乱的“周期性”社会运动在法国多次上演。
尽管当前这场近二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骚乱,在政府出动4.5万警力和宪兵部队后逐渐趋于平息,但深刻剖析背后的根源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举措,已超越其他政治议题,成为马克龙领导的法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政府有力控制事态
面对突如其来的抗议和骚乱,马克龙政府吸取了2005年社会骚乱爆发时的教训,并借助自己上任以来,在2018年 “黄马甲运动”和2023年退休金改革引发的社会骚乱中获取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相对及时有效的举措,使得此次骚乱尽管规模大、破坏性强,但在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基本得到了平息。
首先,马克龙及政府内主要官员采取了及时有效的短期应对措施。通过公开表态、走访警局、举行市长会晤等多重举措积极主动地安抚社会各界,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事件爆发后,马克龙总统6月28日在马赛访问时发声,表示“一名少年被杀,这是无法理解且不可原谅的”。
随后,马克龙又在内阁紧急会议后发表讲话,明确骚乱中的暴力行为亦不可接受。这与2005年两名少年因逃避警察而触电身亡事件发生后,内政部长发声袒护警察引发社会骚乱,总统希拉克直到骚乱持续三周后才公开表态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马克龙的表态,又引起了警察工会的强烈不满,认为总统是在政治和公众压力之下,违背对当事警察接受调查前应作“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干预司法程序。
由于平息社会骚乱必须依靠警察部门的全力配合与支持,马克龙又马不停蹄地于7月3日突访巴黎警察总部,向连日来负责控制骚乱的警方表达支持和慰问。
在此次骚乱中,两百多个城镇的公共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有市长住所遭遇袭击。各个城镇的治理能力在骚乱中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对此,马克龙又于7月4日在爱丽舍宫举行市长会晤,邀请两百多位城镇市长参加,向这些基层社会管理者提供支持,倾听意见,商讨对策。
其次,在事件发生的一周时间内,马克龙政府当机立断地派出了4.5万名警察和宪兵部队维持治安。内政部还向马赛和里昂两个骚乱严重的城市增派了特警、装甲车和直升机等执法力量。
这些有力举措对于快速平息骚乱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最终并未像2005年那样启动国家“紧急状态”。
叠加的社会问题
此次骚乱是法国多重社会问题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穆斯林族裔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
事件一经曝光,“下一个可能是我”的想法,引爆法国以穆斯林青年为主的移民族裔的强烈愤怒,导致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法国全境多个城市。
事件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一特定群体的集体共鸣和应援,和移民难以融入法国主流社会,政治与经济地位不断边缘化等日积月累的社会顽疾密切相关。
法国是欧洲国家中穆斯林移民在数量和占比上均居前列的国家。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协助移民融入的政策,却收效甚微。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在法国社会的融入程度相当低,他们大多聚集在大城市郊区,从事社会底层工作,在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的获取上处于劣势。而他们的孩子,即“二代移民”尽管出生、成长在法国,也难以摆脱这样的社会地位。
对国家缺乏认同,对政府缺乏信任,对社会缺乏责任,使得这些二代移民成为法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常常在穆斯林移民聚集的城市郊区从事贩卖吸食毒品、抢劫盗窃、打砸公共设施、焚烧汽车等违法犯罪活动。“郊区危机”“郊区暴力”早已成为法国社会频繁面临的治安问题。法国政府为此还特地划定“城市敏感区”“治安优先区”等重点治理区域,其中穆斯林移民聚集区占了近一半。
在此次骚乱中,近两百起对市镇大厅、图书馆、学校等社区公共建筑的攻击,也大多发生在这些移民聚集的郊区地带。
其次是青少年教育与就业问题。
根据法国司法部的统计,在此次骚乱的四千多名被捕者中,绝大多数是年轻男性。其中超过1200名为未成年人,平均年龄只有17岁,最低年龄只有14至15岁。男性化、低龄化、暴力化是此次参与社会骚乱的青少年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
社会与家庭监管责任和义务的缺失,是这些青少年成为骚乱主力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骚乱起源地大巴黎地区南泰尔市的一名官员表示,这些年轻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的正在工作,但遭受歧视和叛逆,有的已有犯罪记录。其中大多数人似乎已经辍学,家庭状况不稳定。法国“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尤为明显。他们不惧权威、对峙警察、不听从社区内伊玛目的劝导、在墙上涂鸦“我们就是法律”,抓住任何一次社会抗议活动为契机,采用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对政府和社会的强烈不满。
再次是警察暴力执法和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
多年来,在不断防范和应对法国屡屡发生的抗议、骚乱、恐怖主义袭击的过程中,出于保护警员的目的,法国警察使用武力的权限得到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警察执法不当、滥用武力的问题也随之越来越突出。
2017年,法国修改法律扩大警察用枪范围。此后,每年法国警察对行驶中的车辆开枪数量持续上升,仅2022年,就导致13名青年因此丧生。警方的强制盘查往往以阿拉伯和非裔族群为目标,执法过程中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有罪推定”偏向。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曾多次被国际与欧洲相关人权组织批评,联合国安理会也曾呼吁法国“认真解决执法中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深层问题”,但并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积极回应。
在此次事件中,根据路人发布的相关视频也可以看出,执法警察对于并未对其构成严重生命威胁的当事少年扣下扳机,明显存在“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因此成为抗议导火索。
信息时代下社交媒体也在推波助澜。
社交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快速传播相关信息与非理性情绪的主要载体,助推了抗议质变为骚乱的进程。在TikTok、Instagram和Snapchat等热门社交应用程序上,人们可以通过骚乱参与者或旁观者,以第一视角拍摄的短视频了解最新情况。那些对奢侈品商店和公共设施打砸抢的视频,在许多年轻人中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进一步助长了骚乱。
在突发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中,缺乏监管的社交媒体沦为参与骚乱者组织街头活动、相互仿效暴力行为的重要工具。
四个挑战
尽管马克龙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应对举措成效明显,快速实现了平息骚乱的目的,但是因骚乱而再次揭开的社会创伤,将构成马克龙政府未来的主要挑战,影响其执政重点。
挑战之一:对警察执法的合理约束与警民关系的改善。
其实早在2021年,马克龙就开启了法国警务改革,包括加强执法监督、简化调查程序等,但此次事件证明,在规范警察执法程序和加强执法监督方面,依然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同时,警方在相关视频曝光前对真相的隐瞒,也导致警察威慑力和公信力在民众间进一步受损。
但马克龙政府要应对国内各项改革进程中可能随时爆发的抗议运动,保障2024年夏季奥运会在巴黎的成功举办,都必须依靠警察体系的配合与支持,更要避免警察系统自己走上街头罢工抗议。因此,进一步提高警察待遇、保障警员安全与福利等,也须是法国未来警务改革中的并行之策。
挑战之二:社会分裂的加剧和极端势力的借机发展。
此次事件中,民间发起的两项线上募捐活动成为社会分裂的鲜明体现。一边是为被枪杀少年母亲发起的社会募捐,而另一边则是为补助当事警员家庭发起的捐款。
当同情少数族裔的群体走上街头抗议甚至暴乱时,支持警察的民众则通过捐款的方式表明立场。到7月3日,对后者的捐款已经超过了一百万欧元,总额达到前者的4倍。
这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情绪和立场,还被法国极左翼和极右翼势力利用,“火上浇油”地加剧社会分化。例如,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拒绝“呼吁冷静”并为暴乱者辩护,指出“参与暴动的都是穷苦人”。
当左翼将矛头集中在警察暴力执法上时,右翼则将矛头对准骚乱者。共和党主席埃里克·西奥蒂毫不犹豫地称他们为“野蛮人”,同时严厉谴责“大规模移民”。极右翼“再征服党”党首埃里克·泽穆尔更是否认警察的错误行为,将暴乱解释为“内战……民族和种族战争的早期信号”。另一位极右翼领军人物马琳·勒庞则利用此次事件将自己标榜为“理性之声”,呼吁秩序,意在获得更多中间民众的支持,为赢得下一次大选做好准备。
挑战之三:少数族裔和青少年的社会融入以及社交媒体的有效管控。
马克龙在公开讲话中表示,政府必须“趁热打铁”,在今夏找出问题根源和切实的应对方案。但如何才能解决移民族裔难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难以融入主流社会、频繁遭遇种族歧视等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分属左翼和右翼的官员们存在分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例如,马克龙关于有必要在骚乱期间切断社交媒体的言论,便遭到了包括盟友在内的法国政界的诸多批评,被指责是搞“专制主义”“放弃民主”。更有一些提议难以得到民众认同,例如马克龙提出对参与骚乱的青少年的父母罚款,作为“初次犯错最低代价”等。
挑战之四:骚乱迫使马克龙政府调整执政议程。
马克龙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欧洲领导人,不仅希望在国内推动一系列改革,更希望在欧洲层面推动有利于法国的产业政策、推进欧洲“战略自主”建设、组建欧洲军团等。
然而,当前的国内乱局不仅打乱了其推进国内改革的节奏,更牵制住了其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身影。此次,马克龙不得不缩短参加欧洲峰会的时间,提前回国,还推迟了对重要邻国德国的访问。法国国内情况堪忧,国际声誉受损,也进一步阻碍法国在欧盟以及世界维度上拥有更大话语权。
7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公开讲话中提出用秩序、冷静和和谐来回应这场骚乱。但是在通过警察、宪兵等强力部门恢复社会表面的秩序、冷静与和谐的同时,如何恢复移民族裔青少年内心对秩序的尊崇,如何消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回归冷静,如何实现一个真正没有歧视的和谐社会,都将是马克龙政府,乃至未来更多届法国政府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 2023, biznews. All rights reserved.